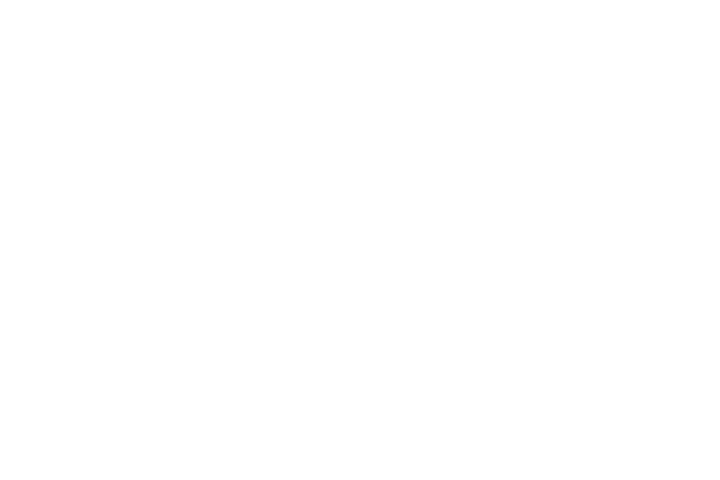20世纪是科学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各项科学技术都在加速发展,把人们带向现代化。在此之前,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麻醉和无菌术也使外科技术在20世纪走向一个全新的高峰。外科医生通过对病变组织的精准切除,使得相当一部分疾病变得可以治愈。但更多疾病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脏器完全失去了功能;其疾病并非因为“存在异常组织”,而是因为“不再存在正常组织”。这时切除也失去了意义,唯一的方法就是将这个脏器换掉,也就是器官移植。
对器官移植的尝试由来已久,但人们发现移植后的器官常常没有功能,甚至坏死。20世纪初的医学界将屡次失败的经验归结为一种神秘的“生物力”,是这种“生物力”在阻止个体间的器官移植。直到1954年,器官移植之父默里采用同卵双胞胎供受体,世界上才首次出现了成功的器官移植。但在更具有普适性的异基因个体之间,阻止器官移植的“生物力”仍然很难控制。当时人们的手段相当有限,全身辐射辅以骨髓移植是当时常用的方法,可这对人体损伤实在太大,难以推行。此时,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有效的免疫抑制药物能协助器官移植手术成功施行。
1969年,在瑞士的山德士Sandoz公司,研究员Z.L.Kis在筛查土壤样本时分离出一种叫多孔木霉的真菌。受益于数十年前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青霉素的启示,当时微生物的代谢物常被提纯后检测是否具有相似的抗菌性质。多孔木霉的代谢物提纯后被命名为环孢素。然而这种化合物的检测结果显示,它并不存在抗菌活性,少量的抗真菌活性也不足以使其成为抗真菌药。这时谁也想不到,埋没于山德士公司庞大药物库中的这份平平无奇的化合物,会在10年之后为免疫抑制和器官移植领域写下划时代的一笔。

在环孢素发现的同一时期,山德士公司正在进行免疫抑制药物的系统性研发。当时肩负这一希望的最佳药物其实是Ovalacin。它的免疫抑制活性很高,甚至超过后来真正上市的环孢素,只不过过高的毒副作用使得这一药物无法在临床研究中继续研发下去。Ovalacin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研发过程留下了完整的免疫抑制药物的试验体系。在研发的同时,山德士还对化合物库中已有的多种药物进行了广泛筛选,这一筛选项目使得环孢素崭露头角。检测环孢素的化学性质时,人们发现,这一真菌代谢物在抗菌之外,居然还有相当可靠的免疫抑制活性。更重要的是,相对于Ovalacin,环孢素的药物副作用要低很多,其性质甚至“过于美好,而令人不敢相信是真的”。
1976年,环孢素首次应用于器官移植的动物模型并发表学术论文,这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时距离默里的首例移植手术已经过去20年,人们已经意识到器官移植后需要免疫抑制来去除所谓的“生物力”,来维持移植物的存活。1950年代末期,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的发现,也为这种“生物力”提出了较好的解答(MHC沿袭至今仍是今天移植前配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当时各种免疫抑制药物的作用效果都缺乏特异性,副作用巨大。1959年发现了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6-巯基嘌呤,首次将肾移植术后1年的生存率提高到65%。在此之前,这个数字甚至不足10%。但此时器官移植仅在第1年存在65%的生存率,作为一种疗法而言,它事实上还无法落地。而经历了曲折的研究和临床试验后,1983年,环孢素的第一个商品药Sandimmune通过FDA审批,首次在瑞士上市,正式用于临床。这一药物使得肾移植的治疗效果大为改善,将移植肾的3年生存率提高到80%以上。这意味着“生物力”的屏障可以被有效打破,器官移植具有成为一种成熟疗法的巨大潜力。
在环孢素之后,各种免疫抑制药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使得移植物术后预后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在器官移植之外,环孢素也广泛应用于其他各种免疫性疾病,如再生障碍性贫血、反复流产和狼疮性肾炎等。环孢素由于其稳定的免疫抑制效果,也被一直保留在今天的肾移植标准免疫疗法方案之中。
文 | 曹懿睿 插图 | Shirley
本文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移植”公众微信号原创文章,转载需经本微信号和原文作者授权并标明出处。关爱肾脏,从关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移植”公众微信号开始 ,您也可以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肾移植术后肾性骨病的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