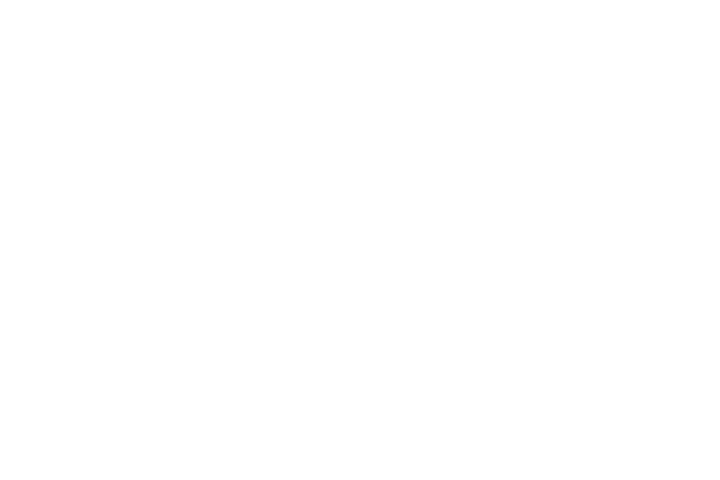文|阿甲
画|马桶
我小时候是在浏正街小学里长大的,因为我妈妈是浏正街小学的老师。
我记事的时候,浏正街小学叫燎原小学,我家住的教师宿舍就在学校里面,是一排低矮的小平房,前后两间,后面有厨房,厨房后面是一个院子。平房前面,有几个水泥乒乓球台子,再前面是礼堂,过了礼堂就是大操场,操场尽头就是教学楼了。
浏正街小学对面是肇嘉坪小学,当时叫工农兵小学,现在是长沙广播电视大学浏正街校区。每到星期天,我妈妈就夹着一叠纸衣样子,去对面的工农兵小学找她的闺蜜,给我和姐姐裁新衣服。
夏天傍晚,晚饭后,家家户户都把竹铺子搬出来歇凉,大人们摇着蒲扇赶蚊子,聊家常。小孩子玩手电筒,扮鬼脸吓人。还有老师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看牛郎织女星。下半晚,父母会把熟睡的我们抱进屋里。

冬天,妈妈把我们摁到被子里面,灌上热水袋,给我们读《鲁宾逊漂流记》。具体的故事记不清了,只记得我盯着家里散发着黄色光晕的灯泡,在妈妈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中沉沉睡去。
时常有调皮伢子被我妈妈留校,趴在乒乓球台上写作业。我妈妈一边生火做饭,一边指导抓耳挠腮的学生们。有时爸爸下班回家,趁妈妈在厨房忙碌,会擅自作主把留校的学生放回家。
天气好的时候,爸爸在平房前面做藕煤,有得闲的老师来帮忙,我们姐妹就在旁边玩煤灰。藕煤晒干后,我们和大人一起一块块搬进厨房。
最开心的是帮妈妈洗被子,光着脚,卷起裤腿,在大盆子里踩被子,名正言顺地玩水,还不被大人骂。
礼堂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怕只有十几吋,做了个木箱子外壳,搭几张桌子,高高的放在主席台上。毛主席逝世的那天,全体老师和家属都挤在礼堂里,抬头看电视里播放葬礼,不时有低低的哭泣声。我们还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跟着大人一起哭。
操场是一个小足球场,周围有体育老师用白石灰画的简易跑道,还有沙坑、爬杆等一些简单的体育设施。小时候觉得那操场真是大啊,每天和小伙伴们在操场里疯玩,直到断黑,父母们穿过礼堂,我们一个个被喊回家吃饭。
那时候的细伢子很少有不挨打的,打人的工具主要是笤刷,就是用布条扎几根竹扫把签子。我家也有笤刷,放在柜顶上,主要起震慑作用。有次,我和姐姐用椅子搭凳子,偷偷把家里的笤刷取下来扔掉,被爸爸发现后,扎了一把更大的,我们就放弃了无谓的抵抗。
虽然一般不用,但我们也尝过笤刷的滋味。有一回,我和姐姐玩寻宝游戏,姐姐把脖子上的家门钥匙埋到沙坑里,由我去找,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也找不到了,回家吃了一餐笤刷丫枝炒肉。
挨完打,妈妈责令我们站在厨房外的院子里反省,我扯着还在抹眼泪的姐姐的衣角,问:姐姐,你还痛不,我不痛了。妈妈听见了,又好气又好笑。

姐姐小时候比我挨的打要多,我妈送她去学二胡,不想学或学不好,就要挨打。每天晚饭后,妈妈一边织毛衣,一边守着她练习,有时拉错了,顺手就用毛衣针打手板。
那时候不懂大人的苦心,妈妈是怕她以后上山下乡吃苦,学一门乐器,将来可以进文工团。姐姐也是争气,小学就参加了市青少年宫的红领巾歌舞团,稳坐二胡头把交椅。后来文革结束了,知青都回城了,妈妈就不要求我学才艺。
学校出门是一条小巷子,巷子口有一家粉店,光头粉一角,肉丝粉一角一,味道特别好。桌上有盐和干辣椒粉两个坛子,勺子是用骨头做的,每次只能舀一点点。我每次生病,就可以一个人享受一碗肉丝粉,唇齿留香,病也好了一大半。
出巷子向左拐,再右拐,就到了藩后街,这是我童年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和父母去菜店、肉店买菜,跟姐姐一起去酱园打酱油,都在这条街上。
上小学一年级后,快乐就少了许多。我妈妈对我的班主任老师,也是她的同事打招呼,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不听话就授权他可以打。
我记得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姓凌,四十岁上下,个子很高,文革期间因打成右派,一直单身。凌老师真的把我安排在第一排他右手边那个位子,上课稍有走神,就用教鞭敲我。这让我在同学面前很没面子,人也慢慢变内向了。
记忆里,妈妈当班主任,早上没时间管我们,上学前,辫子都是爸爸扎的,总是要等预备铃响了,才匆匆忙忙顶着爸爸扎的辫子,嘴里咬着早饭,抓起书包,跑过大操场,气喘吁吁赶到教室里,开始一天的学习。
小学四年级时,妈妈工作调动了,爸爸单位分了房子,我们一家搬离了浏正街小学,小学毕业后,基本上就没去过了。

那时候日子很慢,常常盼望着快点长大。后来长大了,又觉得日子过得飞快,童年的时光是那样遥远。
早几年,我和老公去那边办事,特地去了一趟浏正街小学,站在铁栅栏门外向里面张望,全然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大门变成了拱形门,印象中的大操场也不见了,巷子也没那么长了,前后左右都盖起了楼房。
还没等我感叹,一个年长的门卫出来,问我们做什么的。我一吐舌头,说,没事看看,马上就走,然后牵起老公落荒而逃。
作者介绍:阿甲,土生土长长沙妹子,80年代的文科生,业余码字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