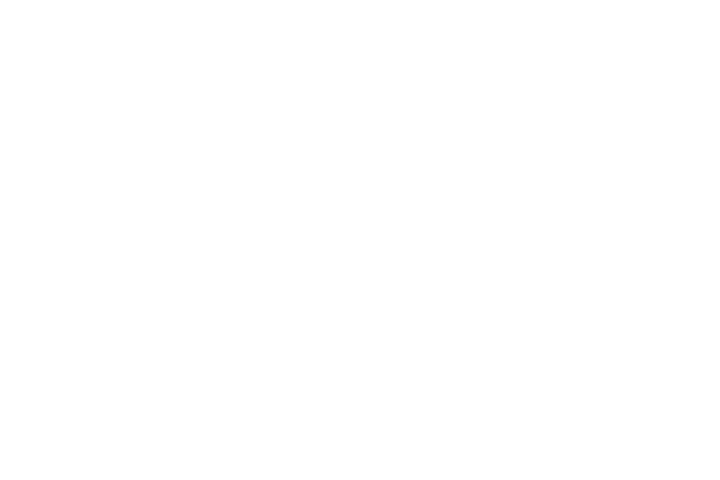再过一些日子,外婆的忌日就要到了。
每当想起外婆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熟悉的画面:在一栋木房子的堂屋里,外婆和外公正对坐在门口。
外婆熟练地扯着棕丝,然后捻成一缕,非常默契地递给旁边的外公,外公接过两缕棕丝,往手心里轻轻地吐上一点口水,随着两只手的来回搓动,两缕棕丝欢快地左右交替跳跃起来,不一会儿,一根棕绳就从外公椅子后面延伸出来。
这棕,有时候是外婆自家烟火山上产的,有时候是到附近集镇赶集买的,搓棕绳卖钱是外婆和外公挣钱的主要来源。一年四季,外婆家里都会备有少量的棕,只要手头有空,就会拿出来捻棕丝、搓棕绳。外婆家的棕绳,因为匀称结实、品相好看,深得收货郎的喜爱。每隔一段日子,就会有收货郎竞相上门前来收购,说外婆的棕绳最适合制作绷子床。
听母亲说,外婆一共生育了九个儿女,最终养大成人的只有五个,其他四个因患天花等疾病不幸夭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湘西农村医疗卫生简直就是一片空白,一旦生了大病,如果土郎中用土办法救治不了,那基本上就只能听天由命,坐在家里等死。母亲曾经说的一个细节,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免心有余悸:我一位夭折的舅舅,在得了天花之后,浑身长疮流脓,大热天躺在床上,身子和床垫经常粘在一起,为了让我那舅舅的身体干燥舒服一些,外公每天从生产队收工回家后,还要连夜用石磨推一两斗荞麦粉,时不时地往床垫上撒一层。即便这样,最后还是没能挽救回我那舅舅的命。无法想象,那个时候,外婆和外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四个孩子先后被病魔折磨而走,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痛苦、煎熬、绝望和无助!
年轻时经历过丧子丧女之痛,外婆和外公的性格反而变得格外开朗,思想也非常开明。抚养长大成人的五个子女中,没有留一个在身边给自己养老送终,一个儿子年纪轻轻就参加工作去了湖北,四个女儿也相继嫁往周边乡镇。平时,二老都是独自生活,只有二老过生日或端午节、重阳节、春节等逢年过节时,大家才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短暂团聚。
俗话说,爹娘最疼断肠儿。或许因为母亲是外婆的幺姑娘的缘故,外婆爱屋及乌,对我也格外疼爱。门前的核桃、橘子、梨子成熟了,她总是要把最好的留一份给我;姨妈和老表们给她买的糖食果饼,她总是舍不得吃,非要留在那里等我去了才肯拿出来,说这是强哥买的,这是娅姐买的,这是单英姐买的,那又是哪个姨妈买的,边说边一把把抓起来往我口袋里塞。特别是每逢过年,她总是把炖好的鸡腿给我留着,每隔一会儿就和外公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把手横遮在眉毛上方,眯着眼睛,向我们前去拜年的方向眺望,只要看到我们母子从远处公路转弯的地方一冒头,裹着“三寸金莲”的她就会拄着拐杖,和外公一同沿着公路前来迎接我们,吃饭时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把鸡腿夹给我。
当我读高中和大学时,为了节约往返路费,基本上都是一学期或一年回家一次。每次去上学时,为了看望外婆外公和节省路费,我都会先步行十几里山路,走到外婆那里上车。放假回家时,一般也会先在外婆那里落一下路,然后再走路回家。一到外婆家,不管你吃没吃饭,也不管你饿不饿,外婆都会颤巍巍地一手扶着板壁,一手拿着升子去里屋舀米或取面条,边做饭边一个劲地自责道:“哎!现在老了,动不起了。只吃得,做不得,又不早点死,要是早点死哒,你们当外孙的也不用这么远天远地地跑来看我们了。”
外婆是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去世的。当时正值五一放假,河里刚刚涨了一次大水,为了少绕十几里路,我回家时就没有在外婆家落路,心想等河里水消了,节后上班去时再看望外婆和外公。回到家里,刚刚从外婆那里探望回来的父母,得知我没有在外婆家落路,便告诉我,这段时间外婆身体不好得很,在病床上经常念叨着我,还替我的工作担心,恐怕时日不多了,要我第二天赶快去看看外婆,他们过两天再去,不然家里没人喂猪喂牲口。谁知,第二天我才远远看见外婆的房子,就听见那里传出一阵阵沉闷的锣钹声,外婆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作为外婆在生时格外疼爱的外孙,为了回家少绕十几里路,从外婆家门口经过都没有落路,在外婆生命的最后时刻,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为她老人家送终,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斯人已去,物是人非。弹指之间,外婆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她当年居住的地方早已变化了新模样。现在,每次路过外婆的老屋场和坟墓前,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外婆,她的音容笑貌如同电影般一幕幕从脑海里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