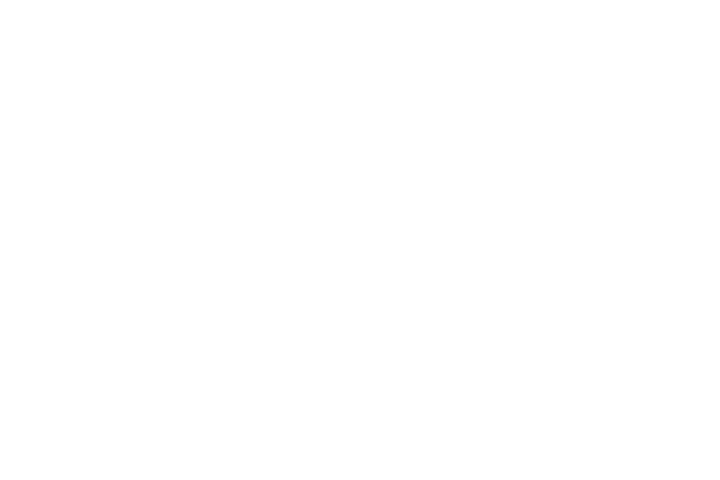童年乃至少年,我都没有离开过家乡。以至于有一次,当兵复员回来的弟弟嘲笑我,你是连省门都没有出过吧?
01
站在后山最高的石块上,我屏住呼吸,引颈静听,每次都只能听见山风穿过树林的丝丝切切的声音,画眉鸟在林间扑腾跳跃,长尾巴锦雉在金色的松针丛中追逐嬉戏。
为什么我从来都听不到火车站的钟声呢?我曾听老人说过,一个人要做到千里眼顺风耳,那必须得有神仙点化,渡劫飞升。于是,我总是期待着,某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会有何仙姑或者吕洞宾之类的仙人,指点一下迷津。
我倒没有期待自己成为神仙,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神仙的法力就不错了。然而,我这似乎微不足道的愿望也是从未实现。也许我的心不够虔诚,也许我根本就没有佛根。
听不到火车站的钟声,我却还有很多做不完的事情。那时候,读书是副业,干活是主业。后山上有整整三个山坡土地,都被父亲和爷爷种上了红薯。种红薯的工序多而繁杂,其中放薯苗,翻薯藤,挖红薯时清理红薯须,这些活儿全部要我参与,每次都让我直不起腰。
父亲说,小孩无腰,青蛙无颈。可是真的,一天晒下来,我也会腰酸背痛。
02
那时爷爷和父亲喜欢抽烟,烟叶都是自家种的。在后山走一个“之”字路,往前就是一大块旱地。父亲把烟草就种在这里。后山的烟草很茂盛,每片烟叶都生长得无比厚实而肥大。每年秋天,父亲都能收获几捆烟草,这便是爷爷和父亲一年的零食。烟草就是爷爷和父亲的力气来源,疲倦不堪的时候,用薄薄的纸片包一撮烟丝,然后细心地紧紧地卷起来,最后用舌头一舔纸片末端,贴紧,一个喇叭烟卷儿就做好了。
爷爷和父亲吸着烟卷儿,半天从鼻孔里冒出白色的青烟,一会儿就飘散了。有时父亲也会被烟呛着,就急急地咳嗽,仿佛咳嗽都很兴奋。那时候,天空有些蓝,但更多的时候是干净的白色,几朵更白的云悠闲自在地停留在空中,好像在陪我们劳动。
03
农活最忙最累的,还要算双抢。水田里的活儿又脏又累。一下田,就是一身泥。双抢季节正是仲夏时分,温度高到爆表,天空中除了惨烈的白,云朵都不知跑哪里去了。那几天,天还没亮,我们家里老少齐上阵。等我开始下田出力做事时,我的三个姐姐都已经外出打工去了。
我带着弟弟妹妹去田里割稻子,父亲就做准备,土车子、箩筐、麻袋、绳子……最头痛的是搬打稻机,那家伙,笨重极了。爷爷过世之后,我成了劳动力,要和父亲去扛那个打稻机,父亲扛的是那个有铁滚子的一头,我扛着桶箱的那一头,从家里扛到田里,足足两里路,父亲的肩头生满茧子,而我稚嫩的肩头被磨掉了皮,露出鲜红的肉,汗水一流,就像被辣椒水浸泡一样,嚯嚯嚯,那滋味,够劲爆。
打完稻子就连夜犁田,三家人家分到的一头老黄牛,累得吭哧吭哧只喘气。母亲照例是要打个鸡蛋煮一瓢米给老黄牛吃的,这待遇,一年可只有一次,要知道,我们自己都一直吃的红薯丝煮饭的。
大概一天时间,有时也会要两天时间,田已经犁好了,就要抓紧时间插秧。又是天刚蒙蒙亮,我和弟弟妹妹下秧田去扯秧。二亩几分田土,也就两三天就要全部搞完。什么活都不会干的我,一年一年劳作下来,竟变成了一把劳动的好手。
04
这样劳作的岁月都是历史了,就那么十来年时间,后来农业生产大变革,有了机器,有了新的种植技术,人工就慢慢的都少了。
后来,父母搬到了新房子里,老屋已经整理成一块平地,我也好多年没有回老屋看过了,老屋后山上的那些曾经给过我许多动力的美食,已经成为记忆中的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