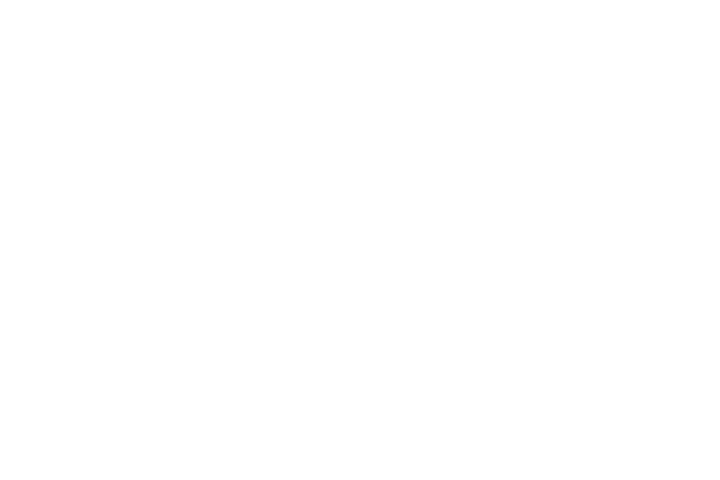文、图|枬子
编辑|马桶
前面两篇:
【长沙往事】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
【长沙往事】从稀烂的平房到湖橡分的大两室一厅
灾难就像一块大铁板,它不由分说地从高空中落下来,咣啷一声砸到你头上,你基本来不及做丝毫的准备。1983年,合理家里的生活逐渐走向正轨之时,雄叔的病情却恶化了,年轻时的肺结核转为肺气肿,又影响到心脏,成了肺心病。重复住院治疗屡次后,终于还是放手而去,分开了这个他颇为留恋的世界。享年52岁。
出殡的那天,下着雨夹雪,西北风吹来,雪粒像沙子一样打在脸上,曾姨的心里像结了冰似的一阵阵发麻。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她没有和雄叔发作过任何争持,无论大事小事,雄叔都极端尊重本人的意见。
雄叔是个超级悲观的人,他的口头禅是“人只需活得快乐,穷也不怕,苦也不怕”,这话听上去像是在宽慰人,拟或自我麻醉,以为是被穷折腾成这样。实则不然,关于灾难,你越是惧怕、恐惧,它越是环绕在你心头,挥之不去。而当你笑着面对它时,灾难即便没有落荒而逃,对你的伤害也会减轻很多。

帅气的雄叔
往常雄叔走了,留下曾姨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燃眉之急就是不能让83岁的家娘晓得真相。这些天,各路亲戚朋友走马灯似地来交往往,早就让下不了床,睡在后屋的老太太心生疑惑。大家磋商着骗她说是把雄叔接到大妹妹那边去疗养,大山里面空气好,对治疗肺病有协助。老太太半信半疑,却也只能置信这种说法。
另一件烦心事就是那些所谓的好意人的纠缠,雄叔走了还不到一个月,就开端不时有人上门给曾姨做引见,发动她再婚。曾姨年轻时是厂里有名的大美人,今年才45岁,厂里和周边单位的确有好些丧偶的适婚对象。她们一进屋就开端各种巧舌如簧地描画曾姨再婚后的幸福生活,搞得曾姨不胜其烦。碍于后屋还有个脚腿不便但耳朵灵活的家娘,又不好大声呵责。最后只好只好在门外贴上一张:家有老人,不喜吵闹,恕不见客,有事请白昼到车间找我。
曾姨拒绝的理由也简单:孩子还末成年,家娘尚在人世。
独一让人宽慰的是,不到16岁的儿子像变了个人似的,忽然成熟懂事起来。每天放学准时回家,晚上和周末也不和以前那帮狐朋狗友进来混,不是帮本人做家务,就是在后屋陪娭毑聊天。可能是父亲的过世让儿子有了义务感吧。
第二年儿子要参与高考了,没想到的是,儿子宣布不参与高考,他要去当工人。曾姨语重心长地劝他去考大学,他理直气壮地答复:“首先,成果普通,考也一定考得起。其次,家里不可能同时养两个大学生。再说,我上大学去了,屋里娭毑谁来照顾?”
拗不过儿子,曾姨只好随他去了,儿子当了工人,特意值夜班,保证家里有人。
雄叔过世五年后的1988年,他娘终于过世,其实老人家生命的最后几年,心里早就分明本人的儿子已不在人世。见惯大风大浪的她,晓得家里人不通知她的缘由,也就装疯卖傻,不想添加大家的心理担负。老人家活到88岁无疾而终。
儿子也在这一年辞去工作考上了大学,女儿给曾姨(如今应该叫曾娭毑了)添了个外孙女。曾娭毑过上了含怡弄孙的幸福光阴,根本上半年在长沙,半年在南京女儿家。
光阴如水,就这么平平淡淡地流淌着,曾娭毑过了十多年幸福而繁忙的生活,带大了外孙女又带孙女。直到2000年查出患上了胰腺癌,与病魔抗争了几年之后,2005年分开了人世,享年67岁。

曾娭毑年轻时跟崽女合影
娘老子的癌症第二次转移后,一拖就是几个月,到最后形容干枯,瘦到只要五十多斤,长期昏迷不醒,就靠着输液来维持生命体征。最后连医生都看不下去,做我两姐弟的工作,说是做儿女的尽孝只能做到这种地步了,再拖下去没有意义,还不如把输液停了,让她老人家早点摆脱。
两姐弟一磋商,无论如何下不了这狠心,还是选择继续拖。娘老子的这场病,固然医药费报销了一局部,但两姐弟还是用掉了大几十万,当然这其中有局部是我姐姐往复澳洲的机票。到最后我已是弹尽粮绝,只能靠姐姐的钱来支撑了。
后来两人都慨叹:搭帮两姐弟还争气,要是经济情况普通的家庭,肯定接受不了。娘老子像是晓得我的困境似的,在病床上坚持六个月后,宁静地分开了我们。
娘老子弥留之际,只断断续续说过几个词,听得清的只要“雄哥、嗯妈、高压裙”。我们剖析她的意义是,要和爷老倌合葬,并且要离外婆的坟不远。就选择在外婆所在墓园的同一座山上择了块地,将爷老倌的骨灰也迁来与她合葬。
我姐姐没明白“高压裙”是什么意义,来问我。我听了心如刀绞,这还是我小时分给娘老子许下的诺言,说是未来参与工作赚了钱,就给她买条当时盛行的裙子。后来哪里会记得,固然赚了钱也给娘老子买过些礼物,但多注重适用性,历来没有思索过她真正喜欢什么。
娘老子的过世对我打击很大,忽然觉得人生没有了方向,没有了寄予。爷老倌走的时分我还小,只晓得家庭的担子要由我接过,这么多年忙繁忙碌地打拼,没有顾得上照顾娘老子,本人搬了家,固然特意留了间房给娘老子,她却还是喜欢一个人住在湖橡。如今回家看到那间留给娘老子住的空屋子心里就难受。娘老子事事为我着想,什么事都让媳妇作主,这样子家里氛围才调和。她最喜欢孙女,我却借口女儿要上好多课外班,一两个星期才带女儿去一次娘老子那边。
娘老子终身命苦,幼时即遭家庭变故,十三岁停学出来打工养家,结婚以后,爷老倌身体又不好。爷老倌中年离世后留下一个瘫痪在家的娭毑,和一双在读书的儿女需求照顾。娭毑百年之后,儿女相继结婚生子,好不容易孙女、外孙女大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却没有过上几年好日子。
我懊悔这些年没有对娘老子再好一些,娘老子在时,我努力工作,想让娘老子为本人的儿子有长进没有孤负爷老倌临终的嘱托而骄傲,如今什么动力都没有了,忽然觉得本人人生没有了期盼和目的,继而低沉,几个月都没有去上班,后来痛快辞职了事。

娘崽合影
那段时间我每周都有几天,会单独开车去父母的坟上,默默地坐在坟前抽烟,一坐就是一整天。回想过往的点点滴滴,忽然发现本人对娘老子并不理解。小时分主要是娭毑和爷老倌带我,我自然和爷老倌更接近。娘老子是全家独一上班养家的人,下了班还有做不完的家务,我和她并没有几交流的时间。
我自小淘气,犯了错,爷老倌批判教育我,她不吱声,只是默默地在一旁听。不过一旦爷老倌入手打人,她总是第一时间冲过来护住我。姐姐总是说,其实娘老子才是那个最溺爱我的人。八十年代后期,她请娘老子去上海旅游,在南京路逛了一天,本人什么都没买,却排了一个多小时队,给我带回一件我喜欢的金色夹克。
当年我迟迟不结婚,最急的是娘老子,又不敢念我。只需看到有女性朋友上门找我玩,她就快乐,总是在三分钟之内就消逝在门外,留空间给我。又或是飞快地溜进本人房间,把房门紧锁,声称本人要睡觉。只差明示:儿子,赶快把人家推倒吧。
娘老子固然没读几书,却自有一种共同的审美情味。细伢子长得快,小时分我每年的毛衣都要被她拆洗后重新织,加些别的毛衣上拆下的瑕疵毛线,每次都能够织出与众不同的效果。

我娘编织的局部作品
她有一双巧手,除了用粗毛线织衣服,还能够用细毛线来钩薄薄的裙子。我女儿从出生到她娭毑过世,身上的毛衣就没重过样,各种把戏创新。有时我突发奇想,设计件款式奇特的衣服,只需跟她讲个大约,都不用画图,十来天时间就能够编织出来,跟我想的丝毫不差,以至比我设计的更圆满。
看着我天天朝气蓬勃,无心工作,不少的朋友劝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现象,谁都会老都会面临死亡,心态正常的去面对。本人过好了,父母在天之灵才会得以抚慰。你咯样,父母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你女儿如今小学都冇毕业,你更要打起精神来把她培育出来,才对得起曾姨不。”
我还反过来教育他们:“我也劝你们一句,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与其在父母逝世后诸多懊悔痛苦,不如在父母尚在时多陪陪他们多尽心。你们的父母都还健在,更要好好尽孝。”
道理其实我都懂,就是心里迈不过这个坎。有天我又一个人坐在坟前抽烟,心神有点恍惚,不知从哪冒出一只白猫,大大咧咧地走到我面前,前爪往我鞋上一搭,启齿讲话:“你何解天天来?” 居然是我娘老子的声音。
吓得我一激灵,差点瘫到地上:“嗯妈,你何解变哒一只猫?”
猫瞪我一眼:“还不是看你天天来,只好寄身猫上来劝下你,以后一年只准来一两次,平常好点在屋里把我孙带好,我走哒。”
我连连点头,看猫要走,忙央求:“嗯妈你在天上过得还好吧?你跟我扯下谈再走。”
一人一猫坐在墓前聊天,更多的时分是她讲我听。聊的多是以前的琐事。她讲她最不懊悔的是和爷老倌在一同,她那时和我如今一样,心里一片灰暗,看不到出路,每天只知机械地工作,回家照顾妹妹们生活。幸好遇到爷老倌这样一个境遇跟本人相同,以至比本人更惨的人,却很悲观开朗,教会了本人要积极面对生活。不论过去、如今是怎样的困苦,生活却总是要继续下去。
就像余华在《活着》里写的那样:人是为了活着自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我正听得认真,却有人摇我:“醒醒,不能在这睡,都五点多了,陵园晚上要关门的。”
我这才晓得原来是南轲一梦,我在父母墓前睡着了。一阵风起,似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期的深处吹来,吹得人睁不开眼睛。抬头望去,远方夕阳下,成片的墓碑中,有只白猫正踽踽而行⋯⋯
未完待续
作者引见
枬子,文革初期出生于长沙,做过工人、会计、财务总监。现为资深高级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