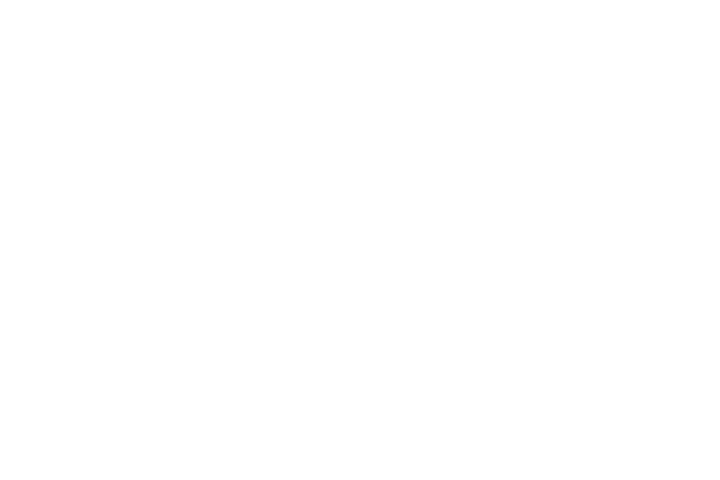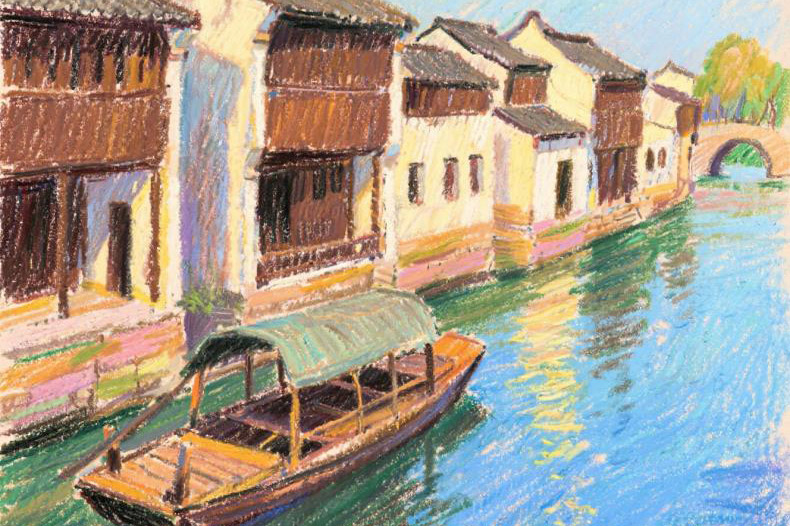
文|枬子
画|马桶
车间里有一批老工人家在乡村,大多是七十年代工厂转向扩展范围时招进来的。说是乡村,其实就是长沙周边的郊县。这批工人多半在熔炼班,也是三班倒,比我们浇铸班早两小时上班,由于凝结铝锭需求时间。
同样是12个小时分三班,每班4小时,我们是从夜里12点到上午12点,他们则是晚上10点到上午10点。这批师傅选择熔炼班的缘由自然是由于能够做连班,连做三个12小时的大连班,白昼就在集体宿舍休息,能够休十来天。特别是农忙时节,有充沛的时间回家干农活。
老邱是个例外,人长得矮壮坚固,一张黝黑的脸,家在长沙城东北边的某个乡,可能是春华乡吧,我记不太清了。应该家里也有地,他却很少做连班,都是正常上班。他在集体宿舍有个床位,平常睡在集体宿舍的时分多,一个月只回一两次老家。
集体宿舍一间房四个人,除了老邱外都是年轻人。我朋友军宝也住这间,我经常去找他玩,跟老邱也混了个脸熟。不过老邱是个闷葫芦,不爱说话,没事喜欢喝点小酒,酒量还颇大。不过大多时分都是自斟自饮,弄点花生米下酒,吃饭就在食堂处理。

有关老邱的事我都是参军宝口中得知,老邱是个鳏夫,四十多岁,无儿无女,一个人过得颇为自由。家里的田也是租给他人在种,自然不用经常回家。军宝说,别看老邱不怎样讲话,其实很好相处,为人也不错。老邱爱听花鼓戏,本人有个小录音机天天听,还跟着哼唱。但只需军宝他们在宿舍,晓得年轻人不喜欢听戏,老邱就自发地把音量调小或是关掉。
军宝他们经常带女朋友回宿舍,老邱好懂味,要是白昼,就会立马出门,而晚上,则是飞速关灯爬上本人的床,放下蚊帐,以示眼不见为净。
我在浇铸班,和熔炼班接触较多,老邱的班次和我相同,经常一同做晚班,关系还算能够。熔炼班的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在大坩锅中凝结铝锭,供我们浇铸班运用。
老邱救过我一次:有天我正蹲在刚铸好的铸件前用锤子打编码——铸件都要手工用铁钎打上一行数字,表示是哪个批次哪个班组消费的——我背后是废铸件堆,翻砂的废品率很高,每天都有几十件废品(当然,废品也可反复应用,清算掉废砂、冷铁后,能够当废铝再次熔炼)。这天的废件很多,堆起来有两米多高。由于要等我们下班后,下午才有人清算,所以暂时没人管,杂乱无章地堆在一同。我正专心打码,老邱从旁边路过,忽然抓住我往旁边一扯。原来是一台废铸件由于没放稳,从顶上滚落下来,正砸在我刚刚蹲的中央。我吓出一身冷汗,几十斤的铸件砸下来,不说有性命之忧,骨折是肯定跑不了的。
我十分感激老邱,自此以后就经常开烟给他,偶然还闲谈几句。
熔炼班最辛劳的是早班,由于要先生火加热坩锅,熔第一炉铝锭最费时间。后面再熔时坩锅是热的,只需求加焦炭就行。老邱做事情十分认真,有一股犟劲,他人点炉子都是用木柴点燃后加焦炭,然后用鼓风机吹,这样最省事,燃起来也快。不过容易损坏坩锅,一只坩锅上理论上能用三四天,这样加热,升温过快,只能用一两天,而且焦炭的耗用量也多。按工艺请求,要先用柴火预热,再放焦炭,熄灭充沛后再上鼓风机。熔炼班只要老邱做早班严厉依照操作流程来,结果就是要提早半小时上班,而且工作量比他人大,招致他的徒弟铁伢子很有意见。
铁伢子满腹怨言只能跟我诉说,老邱管徒弟极严,经常骂他。不过骂归骂,对他还是很照顾的。老邱是教师傅,连车间主任都要让他三分,更别说班组同事了。
我抚慰铁伢子:“你师傅按操作流程做事,也是对的不,只要咯样才学得到技术。”
铁伢子没好气地说:“有么子技术可学,无非就是烧火,搞快点多废几杂坩锅就是,又不扣钱,省哒也不是省本人的钱。”
这话让我无言以对,的确,翻砂车间的工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技术,都是极简单的工作。工厂也不注重对工人的培训,像我在浇铸班工作了几年,也没人通知我工作的原理是什么,只是机械的遵照几分钟让铝水加压至模具,几分钟又放气减压冷却,再几分钟开模。管理上也很粗放,各工序的工人都是只看能如何快速地完本钱职工作,好早点下班,糜费非常严重。
我只好跟铁伢子开玩笑:“你学哒烧火也是技术不,未来当烧火老倌就不要学了。”
铁伢子气得踢了我一脚:“你才当烧火老倌。”接着又低声说:“我看我师父就像个规范的烧火老倌。”

长沙话把跟儿媳有一腿的家爷叫烧火老倌,我就是跟铁伢子玩个谐音梗。忙阻止说:“莫打乱讲,你师傅是个诚实人呢,再讲他又冇崽,何什当得烧火老倌。”
铁伢子撇撇嘴:“那不一定,诚实人特意做扎实事,说不定哪天就有第二春。”
还别说,刚过春天,老邱身上发作了宏大的变化,他也开端做大连班,一回老家就十来天不回来。有天我做中班,早上八点下班后去食堂吃饭,正碰上从集体宿舍出来的老邱。他手里提着大包小包,全身上下拾掇得整齐整齐的,连头发都打理过,隐隐有洗发水的香味。
我打趣道:“邱师傅,回老家相亲去吗?”
老邱黝黑的脸上居然泛出点红色,有点扭怩地说:“家里搞双抢,我回去帮助。”
我有点疑惑,老邱家里的田不是都租给了他人吗?要搞什么双抢?晚上跟铁伢子聊起他师父,他通知我,老邱恋爱了,对象是同村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寡妇。老邱回家就是看他女朋友,顺便帮人家家里的田抢收抢种。
老邱的幸福光阴持续了几个月,和熔炼班其他师傅一样,老邱也开端长期做大连班,一回家就呆十来天。上班的时分看得出心情很好,经常一边干活还一边哼着花鼓小调。脸上的笑容也非常绚烂。话也明显增加,偶然还跟我们聊聊天,骂铁伢子的次数少了很多。熟悉的工友拿他开荤笑话,他也不生气,只是笑笑,不过死活不肯通知我们详情。
有一天我上班遇到老邱,很是不测,就问:“邱师傅,你不是前天才回去的吗?何什就来上班哒?”
“屋里冇么子事,就早点来上班。”老邱的脸色明显不太好。
铁伢子凑趣说:“师父是想我们哒。”
老邱瞪铁伢子一眼:“就你话多,还不打药去。”
所谓“打药”,就是在铝水出炉之前加精炼剂,去除杂质。
铁伢子冲我做个鬼脸,转身去做事。
那些天,老邱明显有点闷闷不乐,又恢复成以前的闷葫芦了。
班上到一半,气泵坏了要维修,只能先停工。我坐到熔炼炉旁烤火休息,老邱在一旁,见没有其别人,悄然问我:“利伢子,你们年轻人谈爱,要是妹子生气哒,何什搞比拟好?”
我当时并没有谈爱,晓得老邱是信任我才会问,想了想,依据他人的经历答复:“妹子生气无非就是哄,再买点礼物就好。”
老邱挠挠头:“那要是哄也哄不好何什搞?”
正好铁伢子路过,听到我们对话,就不以为然地说:“那就打噻,打一顿扎实的,她就听话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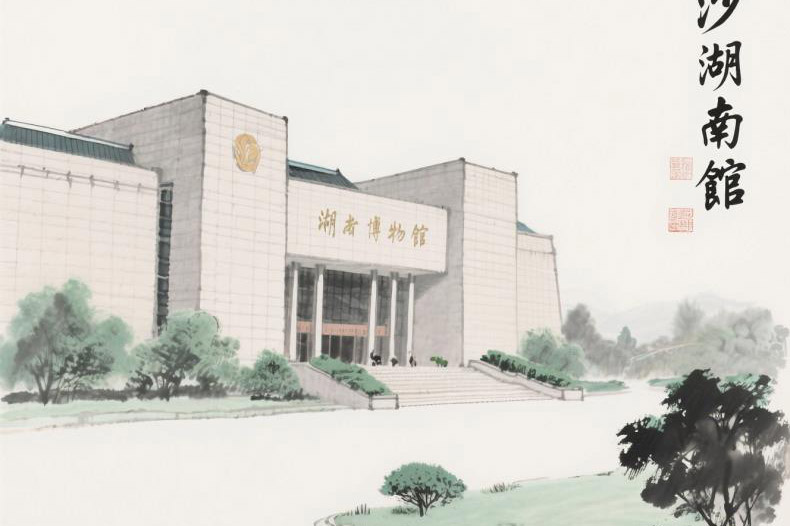
铁伢子结婚结得早,他是个粗人,发起脾气来喜欢打堂客。我们骂过他好屡次,他也不听。
我忙批判铁伢子:“你莫打乱讲,把师父带偏哒,打人犯法咧,再讲会把人打跑去。”
铁伢子不服气:“效果几好,我打一次,她能够听话好多天。”
我没好气地说:“那是你堂客懦弱,换个人看看,不只会跟你离婚,还要告到法院去,把你抓起来。”
我看老邱若有所思的样子,深怕他信了铁伢子的,赶快说:“邱师傅,你莫受骗,千万打不得,入手就是错。”
老邱点点头,没吱声。
没过多久,就再也见不到老邱的身影,工作也被其别人顶替。我才晓得老邱出事了,熔炼班有个工友是老邱的同乡,晓得内情。我隔了好多天,才从铁伢子那里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老邱的村子里有个寡妇,三十多岁,风姿犹存,不知怎样跟老邱厮混在一同。两人交往了几个月,那寡妇不知是老邱不在的时分耐不住寂寞,还是嫌老邱是个粗人,又和他人勾搭上了,对老邱就有点爱理不理的,不过农活还是等着老邱回来做。
老邱听了些闲言风语,心里很不舒适。出事那天,老邱正在田里干活,两人为了这事起了争论,不知寡妇到底讲了什么,剌激到了老邱,老邱大怒之下,随手挥起手中的锄头砸去,正中寡妇的天灵盖,当场殒命。
这个案子案情简单,杀人偿命,没什么好说,不久老邱就被执行死刑。不是什么好事,车间自然低调处置,只要本班组的和几个熟悉的工友晓得实情。铁伢子想拖我去现场给老邱送行,被我一口回绝了。固然是咎由自取,但看了还是会难受。
作者引见
枬子,文革初期出生于长沙,做过工人、会计、财务总监。现为资深高级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