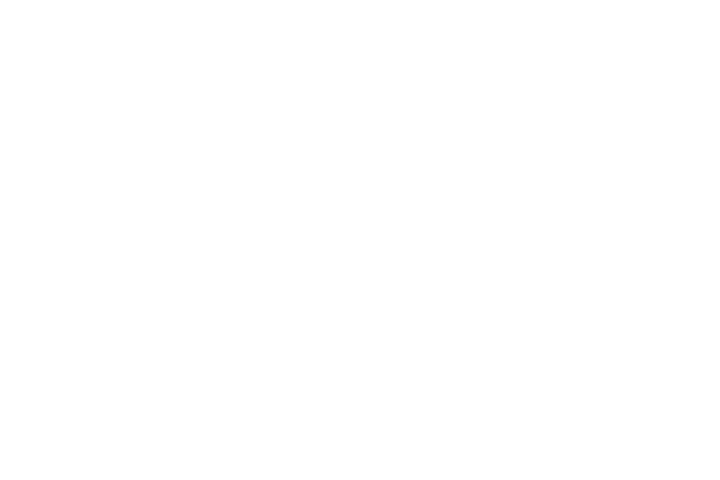文|陈铁男
画|马桶
从小,我就很羡慕有兄弟的人,不是社会上那种,而是扎扎实实的亲兄弟。一起成长和帮助的那段经历,是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同龄的独生子女所没有的。
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认识大毛和细毛,他们两兄弟虽然不是双胞胎,但是长得却一般无二——高高瘦瘦,头发从不修饰,加上猛大的死鱼眼睛,使得他们看上去总是一副蜡霉的样子。如果不是看见过他们爷老倌的桑塔纳和大哥大,我肯定把他们当成两个乡里来的邋遢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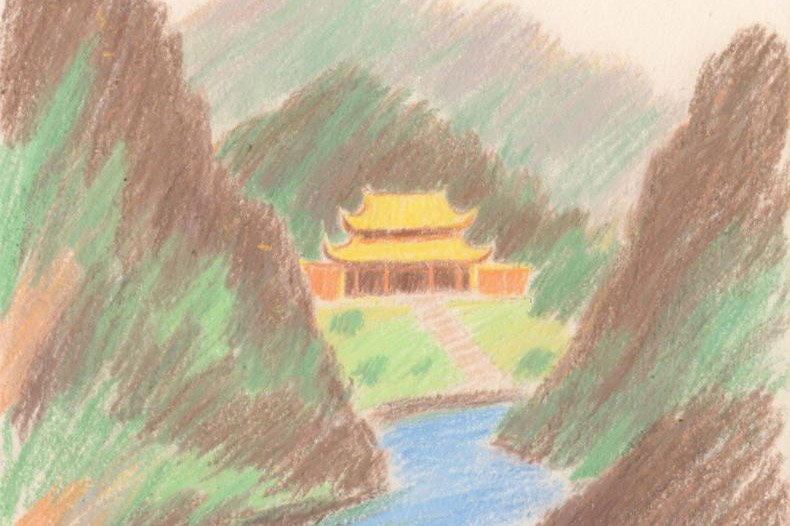
我们那个年代的细伢子不像现在,有手机、电脑还有王者荣耀,小时候的我们,更多的是和附近的小伙伴一起爬得树上掏鸟窝,摘桑叶,要不就是匍得地上拍洋菩萨,或者挖几个坑画条线来“点弹弹”。
大毛就是个“点弹弹”高手。“点弹弹”的时候,他沉着而冷静地趴在地上,像一头准备出击的猎豹,瞄准好后,把头发往后面一抹是他的标志性动作。随着几声“啪啪”的脆响,就把我口袋里的弹弹赢得一粒不剩。
我曾一度认为他这么厉害的秘诀在头发上,我有样学样的在自己头发上抹了一把,却抓了一手的油墁,滑得连弹弹都抓不稳。
弟弟细毛的弹弹技术喷臭的,他更像只撒欢的鸵鸟,一天到晚跑个不停,今天才打烂这个屋里玻璃,明天就掀翻公园里爹爹的棋盘子,每次闯完祸就挂着满脸的眼泪和鼻窦脓找他哥哥帮忙了难。
1997年,我和大毛都考进了长沙市第28中,当年的28中比较乱,有点像是是《热血高校》里的铃兰中学。我曾亲眼看见,有人在学校边上的粉店被打得血湖血海,脑壳就栽得盛汤的炉锅里,把一锅上好的筒子骨汤都染成了红色。
大毛会做人,加上花钱认了几个“老兄”,我们头一年的初中生活也算是无惊也无险。第二年,小我们一岁的细毛也被分配到了28中,在我们几个老兄的关照下更加无法无天,乖戾的性格尽显无遗,常常两句话不对就把人打进医院。
大毛对此头疼不已,不止一次的的劝过他,细毛一句“反正伢老倌有的是钱”怄得大毛发誓再也不管他了。
“那杂化生子,总有一天会出大路的啰!”大毛跟我说。

细毛的大事很快就来了,那天学校门口围了几十号人,从装束和派头看出来都是社会上的流子——他们都是来找细毛的,细毛骇得像个鸡崽子。
他又像小时候那样跑来班上找哥哥帮忙,他的头低到了胯里,两条腿还在不住地打着摆子。
原来,细毛在其他学校把一个人的瓢给开了,而那个被他开瓢的背时鬼正好是某个大人物的独子。如今背时鬼正满脑壳绷带挡在校门口耀武扬威,要不私了,要不报警,留给细毛的选择只有这两个。
报警是不可能的,至于“私了”,自然是几十个人围殴他一个。最后大毛给了弟弟第三个选择——他把细毛交到我手里,叮嘱我要照看好他弟弟,头发一抹,转身就朝校门口走去。
校门口对面是一个汽车修理厂,啤酒瓶子、木棍、窑砖随手可捡,但凡要动手的话,这里必然是首选之地。一出校门,大毛就被那些二流子当做细毛拖了进去。
过了好一阵,流子们终于散去了,大毛才从对面的汽车修理厂走出来,尽管他刻意整理过了衣服,可背后的那些皮鞋印子告诉我,他没少挨打。
“大毛别,冇事不?”我上前搂住大毛的肩膀。
“冇事咧,挨两嘴巴抖一脚的路。”大毛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那我们……搞……搞起回来啰?”细毛这句话说得特别没有底气。
“搞你妈妈X,跟老子滚!”大毛一脚踹向细毛,细毛条件反射的一躲,大毛踢了个空,还差点摔一跤。
就在我以为这件事总算是过去的时候,一个礼拜后的早会上,学校领导却宣布了一纸通知:“大毛因与外校、甚至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打架斗殴,对学校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此做出开除学籍处分,请广大同学引以为戒,广而告之。”
为了帮弟弟“顶包”,我觉得大毛有些可惜。“有么子办法咧?有杂该号不息事的老弟,”他如此说到,“算哒,反正我也不想读书哒。”那天起,大毛就再也没有来过学校。
那是我头一次羡慕细毛,有这样一个老兄。

后来,因为家里的生意,大毛细毛两兄弟搬去了别的城市,我再见到他们两兄弟时已经是二十七八的年纪。
这时的大毛和细毛可以说是荣归故里,从他们开的宝马和奥迪,以及手里递过来的和天下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确实是发财了。
原来,前些年兄弟俩跟着爷老倌在外面接了不少工程,赚了许多票子,大毛就提议回长沙来开个家装公司,顺便韵个当老板的味;又听说我是搞室内的,硬要拉我做他们公司的设计总监。我当下就拍着胸脯答应了,鬼晓得我还只是个刚入门的实习设计师。
“到时候我们一起发财啰。”大毛还是头发一抹。
重逢之后,我就跟着他们整晚过着灯红酒绿的日子。可这样的日子还没过上几天,细毛突然面无血色的告诉我:“何什搞,屋里要破产哒,爷老倌怕么都会关得号子里。”看来,我设计总监的位置是坐不到了。
据细毛说,他们公司的合作伙伴胡老板卷走六千万的工程款跑路了,而他们爷老倌又是公司的法人代表,担心要不到账的债主们纷纷找来,防盗门都锤烂两张了。
当时我不清楚六千万是个什么概念,只晓得他们现在需要钱,我取出几乎所有的积蓄:“细毛别,六千万我冇得,六千我还是有,先拿哒啰。”细毛接过钱,望着我哭笑不得,欲言又止。
突然,他眉头一皱,眼神里露出骇人的凶光,随便跟我道了个别就扭头走了。
很快,我听说他们最终找到了该死的胡老板,追回了绝大部分的钱,公司不会破产了,他们爷老倌也不再面临追债和起诉,之前的一切看似虚惊一场,生活又回到原有的轨道。
“铁男别,帮我看哒点细毛别啰,他那脾气真的要不得,咯多年,不是有老子啊,他早就……”这是追回钱的当晚,在饭桌上大毛对我讲的一句话。

次日,大毛就被呼啸而来的警车带走了。两个月后,他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庭审是在外地,所以我并没有看到,但是据说被害人胡老板当天是坐着轮椅出庭的。
“你要不下那重的手就好哒,最多赔点钱了难的路。”探监的时候我依然为大毛觉得不值。
“你指望胡一刀那号人老老实实的把钱吐出来?”大毛笑了一声,“我是真的冇退路哒,把得细毛别动手看,那就不是五年的事唻,搭帮我先他一脚。”
“难怪,那天晚上我就估计细毛会想搞点么子路出来。”
“冇办法,哪个要我是他老兄咧?”大毛摇摇头,习惯性的头发一抹,又跟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尴尬的把手缩了回去,生怕我看见他窘迫的样子。
今年六七月的某天晚上,我在街上碰到了细毛,他一个人坐在我对面的夜宵摊子,桌上堆起好高的生蚝壳子告诉我,他的性生活太没有节制了。
“老兄,好久不见唻,他妈的,换咖号码也不告诉我,快点来陪我呷酒。”细毛看似比以前稳重了许多,至少把X你妈妈别换成了他妈的,没那么社会气了。
明明是五块钱一瓶的哈啤,没想到也能把我灌醉。当晚我不仅呕了一碗珍珠肉丸汤,还忍不住把大毛跟我讲的话全部告诉了细毛。
听我说了这些之后,细毛半天没做声,只是喝闷酒。十几分钟之后……
“坐得牢里的应该是我,不是我哥哥!”酒醉之中,细毛突然扑得桌上,哭得像个细别崽子。
那天晚上风特别的大,大得我睁不开眼睛。